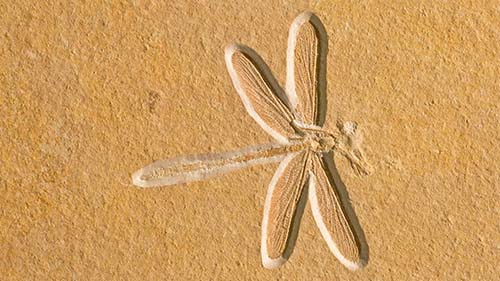中国评剧大剧院(北京中国大剧院演出信息)
“真的八个月没见了!”“哦,是的!”
周日下午2点30分,老舍茶馆曲艺团的架子鼓表演一开始,主持人郑思杰就热情地向观众打招呼,得到了观众的回应、欢呼和掌声。
国庆假期前,北京曲艺团在老舍茶馆恢复演出。在过去的八个月里,由于疫情,这里没有任何民间艺术表演。“北京能听架子鼓的地方屈指可数。疫情期间,我只能听信息磁带,看视频,不在现场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味道!”坐在茶楼里听着鼓声,年过八旬的刘焕荣感慨万千。
北京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何伟伟在北京市曲艺团成立68周年暨恢复5周年系列演出中表演(曲艺团供图)
老观众觉得:不要去天津听。
“请上楼!”顺着门卫的指引,老舍茶馆这个小剧场的二楼准备开船了。台下,久未谋面的观众互致问候;舞台上,演员们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角落里,服务员正忙着给茶碗泡茶。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鼓乐表演。
周日下午两点半,这是北京鼓乐爱好者刻在脑海里的一个时间点。自2015年北京曲艺团重新组建以来,每周日的这个时候都会在老舍茶馆表演架子鼓。疫情发生前,有200多场演出。
北京曲艺团在老舍茶馆的鼓乐表演
"说起北京的鼓,那就一言难尽了."梅花(鼓),丹仙,景云(鼓)...这些鼓源自京津,刘焕荣如数家珍。1993年退休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鼓乐上,甚至为了听鼓乐,他还经常和朋友去天津。
“说实话,北京曲艺的发展还不如天津。尤其是这几年,年轻人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们听曲艺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刘焕荣说,老舍茶馆几乎是北京唯一一个常年坚持表演鼓乐的地方。“天津每天都有一些监听。我们的音乐朋友每次去,都会多待几天,多听一些节目,用设备多录一些片段,让他们玩得尽兴。”
疫情期间,所有剧院都关门了,没地方听音乐的刘焕荣只能拿出家人的资料,在电视上看鼓乐节目,在手机上看视频。“没味道,不行。曲艺,尤其是现场的气氛,台上台下的交流。离茶馆、戏院太远了。”在北京的曲艺表演恢复之前,他忍不住在9月1日又去了一趟天津。听到北京曲艺团恢复在老舍茶馆的驻场演出,刘焕荣和曲友发自内心地高兴。“对我们这里的兄弟总是好的,我们还有优惠卡。一张票的市场价至少50元,只会向我们收取30元。”
不仅是老音乐家,演出现场也有年轻人,还有来体验北京文化的外地游客。“这是好事。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真的很像。希望他们能传下去。”
当演出准时开始时,刘焕荣坐在前排。在舞台上,主持人郑思杰介绍了之一期节目的乐队成员:“这位老先生生病来到舞台上,他的双手已经失去了控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观众都是老观众。请等我。老先生也希望年轻人接手,也希望对观众感兴趣的年轻人也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新老乐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
演员坦率地说:
长期远离舞台,怕包袱不响。
生于80年代的相声演员张天雷是北京曲艺团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他不仅是表演的中坚力量,也是创作的主力。
二环与三环之间,西罗园4区19号,前身是中国评剧大剧院,现为国家地方戏曲表演中心,北京曲艺团临时大本营。北京曲艺团68周年暨5周年系列演出周将于9月22日起在这里举行。
虽然这一天没有演出,但张天雷出席了。他出生在天津,那里的曲艺氛围浓厚。自幼就读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后师从李京,多次登上各大电视台春晚。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离开舞台这么长时间。”在过去的半年里,张天雷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和排练作品,但他没有表演。“我们组的工作安排相当有规律。每年都有固定的剧要创作,疫情期间也有新的题材,完全不能说是闲着。但是舞台真的已经走了很久了。”
相声的创作和排练对场地要求不高,在家就可以完成。疫情一爆发,张天雷就响应团里的号召,开始创作抗疫作品。
“这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的作品了。”张天雷说,作品要有一定的科普价值,不能犯常识性错误。“最重要的是,不要像读手稿一样。没有乐趣,没有可乐,那就太尴尬了。”好在他和搭档郭天一都是天津人,交流排练相对方便。“这几乎和工作一样。我们在家里录了,连夜赶出来报道,领导连夜回应,然后上线。大年初二,忙到第三天。这次“杀毒播报”完成,前后不超过24小时。”
就这样,忙碌了半年,习惯了台上台下热烈互动的相声演员张天雷,几乎成了 *** 的“主播”。“互联网是趋势,我们集团有新媒体平台,我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但是,我们毕竟是国有院团,要遵守一定的创作底线,不能为了好玩就没有底线。像马季先生一样,创作出有风格的好作品是我们的目标。无法实现。坦率地说,这很难,但我们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8月,张天雷之一次见到了观众。“天津电视台的节目在演播室,但还不是剧场,但观众里有人。”说的都是老掉牙的笑话,心里,包袱在哪里早就清楚了,但七个多月远离舞台,还是让张天雷手心冒汗。参加了很多聚会,但这种紧张情绪仍然完全失控地袭击着他。“远离舞台久了,恐怕担子就不响了。观众不高兴怎么办?”好在观众很给面子,该让的担子都让让了。“后来观众说很久没看现场表演了,很怀念。”
因疫情加速曲艺团转型
“我们也想念观众。”北京曲艺团团长王月明在国家地方戏曲表演中心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当他接待客人时,他坐在两个简单的沙发上。“我们剧团还没有自己的剧场,这里的剧场、排练场、办公室都是租的。半年没有演出,房租却要交,压力不小。”
北京曲艺团的辉煌无需赘述。曲艺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梁小楼、关、梁厚民,都曾是这个群体的顶梁柱。就算不懂曲艺,只要看过央视春晚,听过几段相声,就知道李金斗、陈涌泉、笑林、李国胜。
“那是以前。”曾经辉煌过,被并入京剧院舞剧院,后恢复建制。历经68年沧桑,北京曲艺团现为国有企业经营的艺术团。表演,尽可能多的表演,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在王月明的办公室里,你可以听到表演中心的鼓声和观众的掌声。“这种感觉早就没有了。”本来春节假期应该是文艺演出市场最红火的日子,对曲艺团来说是最重要的。“演出计划早就安排好了。”但疫情不知从何而来,从1月24日除夕开始所有演出计划暂停。
“不能说节目停了,只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在新年前夜开始了我们的新工作。”王月明表示,新作包括抗疫题材的作品,也包括寻找使用新的传播手段的方法。“我本来就想改变和转型,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
自2015年重新组建以来,北京曲艺团开通微博、微信账号,疫情爆发。他们开始在Tik Tok、汽车快手、中央视频等平台上发布曲艺作品。起初,像张天雷一样,这是一个简短的科普节目。渐渐地,各行各业都恢复了生产,曲艺团网上的“京味儿剧场”成了演出的主阵地。“线下影院复工比影院更谨慎。”王月明说,演员现场表演,台上台下都有互动。电影院复工后很久,北京曲艺团只能在网上的“京味儿剧场”演出。
现在,终于可以线下演出了,但是线上剧场还是停不下来。“在现场可以真正感受到曲艺的独特魅力。互联网是有用的,它的作用主要是引流、普及、吸引年轻人。”
随着疫情的逐渐稳定,曲艺重新焕发了生机,回到了老话题——吸引年轻观众,培养年轻演员。北京曲艺团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开办了一个少儿培训班,计划寒假继续。王月明说,“一方面是给有兴趣的孩子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现人才。”